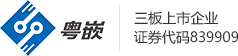手机实名制与现行法律相符
一种观点认为,从法律的角度看,“手机实名制”与现行法律相抵触,应紧急叫停。 因为在实践中,“手机卡”的销售均由通信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商办理,那么这些通信公司怎样才能确认买卡人的身份证是真实的呢?的办法就是查验买卡人的身份证,而依据现行法律和行政法规,经营者(含通信公司)无权查验公民的身份证。根据我国居民身份证法的规定:警察有权查验身份证;公民在办理婚姻事务、兵役事务、出入境事务、户口变更事务时应当出示身份证。此外,还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需要用居民身份证证明身份的其他情形”。可见,除上述列举的事项外,只有法律和行政法规才有权设定公民出示身份证的法定义务,而法律和行政法规只有全国人大和国务院才有权制定,地方任何机关、团体、企业均无权制定。因此,一些试点城市如福建泉州市率先实行手机实名制,进而查验公民身份证,明显与我国居民身份证法相抵触,理当叫停。
笔者认为,从法律角度看,在办理电信业务时,电信用户出示身份证件符合现行法律精神。《合同法》第十二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的合同内容一般包括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作为合同的一类,移动通信服务合同同样具有当事人双方,且不属于即清即结类,用户购买手机卡这一行为仅是属于合同成立,履行合同的开始,因为履行移动通信服务合同是一个较长的过程。既然双方发生提供和接受电信服务关系,移动运营企业、电信用户都享有了解对方基本情况的权利,即知道和自己签订服务合同的当事人的姓名。
因费用原因,众多新型移动通信业务开通与取消,必须依用户意愿而定。电信用户无论是通过营业厅办理,还是通过手机操作,移动运营企业都需要核实一下机主身份,即业务的办理者是否为签约人,或是否取得签约人的授权。如果在移动运营企业没有身份核实环节,谁持有号码,谁就可以办理业务手续,或终止基本业务手续,真正的机主——电信用户的权益很可能受到侵害,例如:手机被盗、丢失等。手机实名制恰恰能保护电信用户的合法权益,尤其是预付费用户。
对办理电信业务是否需要出示身份证件,《电信条例》是有规定的,如第五十九条明确指出,禁止使用虚假、冒用的身份证件办理入网手续并使用移动电话。《居民身份证法》第十三条规定,公民从事有关活动,需要证明身份的,有权使用居民身份证证明身份。移动通信服务合同当事人之一的电信用户除了出示身份证件外,还有什么能更好地证明自己的身份呢?
实行手机实名并未增加社会成本
第二种观点认为,当人们创制某种制度时,除应考虑创制该制度所要达到的目的之外,还应当考虑社会为此项制度所付出的成本。实名制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手机诈骗现象的发生,但社会却要为此付出高昂的成本。
笔者认为,事实上,自电信业务开办以来,就一直采取书面合同的形式,只不过过去的称谓是入网申请表,办理包括移动通信业务在内的电信业务都需要身份证件,只不过某些代理商核实身份证件时,把关不够严格,加之少数地区的移动运营商对此未加严格管理及自身的营业场所也管理松懈。因此,将原来就需要出示身份证件这一环节补上,就认为增加了社会成本是没有道理的。,电信用户到营业场所办理移动入网手续,需要携带身份证件,除了要记得带身份证件外,并没有增加什么费用,也就谈不上电信用户增加什么成本。第二,电信运营企业对照签订的书面协议,核实一下对方当事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等有限的几种情况,与介绍电信业务、回答用户提问相比,占用的这一点时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又有何成本增加,认为手机实名会成倍增加电信运营企业办理单笔业务的时间,则属于无稽之谈。反过来说,即使出示身份证件会使电信用户、电信运营企业为此多支付了一些时间,也是当事人双方应承担的一点社会责任,毕竟社会秩序靠大家维护,人人有责。至于运营额的下降,则更说明手机实名使通过发送短信方式实施诈骗的减少了,设想一下,有正常需求的电信用户不会因实名制而减少使用电信业务或不去办理入网手续。
实行手机实名不侵犯公民通信自由
第三种观点认为,通信自由与通信秘密是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实行手机实名制,不仅是对公民通信自由的限制,同时,当一个公民以实名购买手机后,作为通信秘密重要组成部分的客户资料安全如何保障、由谁保障?因此,在目前客户资料安全缺少有效保护的情况下,实行手机实名制还会涉及到维护社会秩序与保障公民权利之间的博弈。
笔者认为,很多人担心推行手机实名制会造成用户个人信息资料被滥用,侵犯隐私权。其实,这种顾虑是多余的。实行手机实名制并不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查询用户资料,《宪法》第四十条、《电信条例》第六十六条对公民通信权益有明确的规定,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权受国家法律的保护,因国家安全或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也只有法定机关,如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才可以对用户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进行检查。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对电信用户个人信息资料进行检查,电信运营企业及其员工对电信用户通信负有保密的义务。
对诈骗活动惯用的“群发”予以限制、禁止,在技术上应该说是有可能实现的,但这样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无疑这种方式是真正侵犯了公民的通信自由与秘密。目前,应该看到使用群发功能的,除了少数诈骗短信外,更多的是正常通信,如:节日问候、办公系统的短信提示、会议等商务活动的通知等等,如果采取限制群发,则同时遏制了电信用户正常的通信自由,因噎废食是不可取的。电信运营企业无权对信息发送人发送的信息进行监控,更何况诈骗信息与正常的通信信息在形式上并没有区别。如果采取过滤方式,这与擅自拆看公民的信函一样,侵犯公民的通信秘密,以侵害公民通信权益为代价的过滤方式是有悖于《宪法》的。
总之,我们要正确看待手机实名制。笔者认为,指望手机实名举证责任倒置从根本上遏制诈骗是不可能的,因为通过发送短信的方式仅仅是实施诈骗的一种手段,抓住诈骗嫌疑人才是打击诈骗行为的关键,但手机实名起码可以起到威慑作用,即违法犯罪分子少了一条低成本的通信手段。尽管有假身份证存在,那是有关部门如何打击的问题,可以这样讲,手机实名是电信运营企业、电信用户应尽的社会责任。利用手机短信从事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可以归结为两类:一类为利用手机短信作为通信手段从事违法犯罪行为,如:从事卖淫嫖娼、倒卖枪支毒品、买卖假证件等等;第二类是直接利用手机短信实施诈骗行为,即行为人主观上并没有提供商品或服务的意思,收到汇款后便杳无音信,就是所谓的“短信诈骗”。类,交易双方可以直接接触,打击行为人并不难;第二类,交易双方不见面,一般是通过银行卡或账户进行汇款,因为银行业早已实行实名制,理论上查找行为人也不难。对打击违法犯罪而言,手机实名为打击违法犯罪活动提供了又一种有力的手段。打击短信诈骗需要动员包括电信用户在内的全社会的力量,广大手机用户收到涉嫌违法犯罪的信息或广告,应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积极为打击违法犯罪行为提供线索。